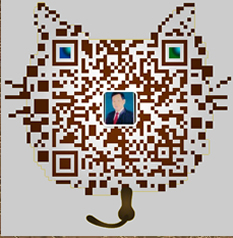一、理论的先行探索
较早的“按责赔付条款”可见之于《机动车商业保险行业基本条款(2007版)》中。[1]
1 . 车损险中的按责赔付条款。《机动车商业保险行业基本条款(2007版)》B款载明:
保险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本公司根据驾驶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负事故责任比例相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保险人或保险车辆驾驶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自行协商或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事故确定事故责任比例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事故责任比例:
保险车辆方负全部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不超过100%;
保险车辆驾驶人负主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70%;
保险车辆驾驶人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50%;
保险车辆驾驶人负次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30%;
保险车辆方无事故责任的,本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按上述约定,被保险人自身责任大,则保险赔付多;自身责任小,保险赔付却小。以至于发生事故后,损失大的一方总喜欢揽责任。这被人形象地称为“按责赔付条款”。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12版)》中已经删除了这样的条款。2014版条款延续了2012版条款的做法。
2 . 责任险中的按责赔付条款。《机动车商业保险行业基本条款(2007版)》B款中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部分存在类似上述的条款。这样的条款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14版)》中仍被保留。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以下简称《江苏纪要》[2]对上述两种类型的条款的效力作出了明确规定。《江苏纪要》第8条规定:对于下列保险条款,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合同法》第四十条、《保险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无效:
……
(二)规定“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机动车辆损失险条款。
(三)规定“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条款。
关于《江苏纪要》作出如此规定的理由,我国台湾地区施文森大法官的论述可谓精辟,[3]关于保险人于车损险得否按被保险人过失比例免责问题:
车损险关于“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约定是否有效?
按车损险为财产保险之一种,存在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适用无过失原理,保险人系以危险事故发生所致于保险标的的损害为承保基础,按被保险人因而所遭受之实际损害尽其损害补偿责任。至事故之发生是否出于被保险人之过失,要非所问。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就此有如下规定:
(1)保险人对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之过失所致之损害负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29条第Ⅱ项)
(2)保险人对于因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之受雇人或其所有之物或动物所致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1条)
以上法条均在宣示财产保险制度之基本理念,具绝对强制规定之性质,不容保险人于其片面预行拟就之格式条款中,减免依财产保险之制度设计及国际既定成例应负之责任。
据上分析,首开约定系将责任保险条款之理念错置于财产保险,意图利用投保大众对保险之无知,经由减免责任以牟取不公平利益之意图,不能更行明显,法院自得依《保险法》第19条规定,宣告其无效。
关于“按比例承担责任”之约定得否适用于商业责任险问题:
车损险关于“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所免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约定得否适于商业责任险,须明确:对危险事故之发生其可归责性为何?若可归责于受害人与加害人双方者,其比例为何?其判断之权在于主审法官。交通主管机关就事故发生可归责性之认定,仅生行政法上之效力,交通主管机关固得据以对可归责之一方科处罚锾或对其采取其他行政法上之措施,但不得径行作为民事赔偿之依据。受害人若采此项“认定书”送陈法院作为其向加害人求偿之佐证者,法官得持以为形成判决之参考,对于双方当事人可归责性之比例仍须审酌一切相关事证而为认定。
商业三责险系以被保险人依法应负之赔偿责任为承保基础。所谓依法包括有管辖权之法院依法所为之判决。商业三者险于保单上约明保险人依被保险人所负事故责任之比例承保相应赔偿责任,与三责险制度设计之原旨无违,当为保险法所许。但若进而声明对同一意外事故被保险人与其他第三人负“同等”责任者,保险人仅付50%之赔偿责任。盖于采用“比较过失”之民事法制下,涉及同一事故之当事人各应负多少过失责任,悉由主审法官斟酌事故发生当时之一切事证,判断个人应负事故之比例,法官于判决中似不可能使用“同等”字样,而保险人亦不得于条款中预行界定共同牵涉同一事故即为“同等”,而对于“同等”即限缩依约应负赔偿责任为50%。
施文森大法官的论述为问题解决奠定了法理基础,江苏、重庆、北京的法院也陆续就此作出表态,否定了“按责赔付条款”的效力。但是,车损险条款中“按责赔付”消亡的直接动因应该还是舆论。2011年期间,这种舆论达到了沸点。彼时,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中写道:
设定“无责免赔”条款,无疑与鼓励机动车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的社会正面导向背离,也不符合投保以分散社会风险之缔约目的,同时有违保险立法尊重社会公德与诚实信用之原则。确认“无责免赔”条款无效,符合正义这一法则的基本价值,亦符合社会和谐发展的科学内涵。[1]
在舆论的浪潮中,车损险中的“按责赔付”条款终于被推翻。
2012年,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加强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保险公司不得以放弃代位求偿权的方式拒绝对机动车损害进行赔偿。这意味着,车险理赔中被誉为“霸王条款”的“无责不赔”将被叫停。[5]但责任保险中的“按责赔付”条款却因为许多暧昧的因素被保留了下来。[6]事实上,按施文森大法官的分析,责任保险中的“按责赔付”条款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限定了赔偿责任的具体比例。仍以《机动车商业保险行业基本条款(2007版)》B款为例。依该条款,保险车辆方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不超过50%。而按现行交通事故法律制度,对机动车方和非机动车方实行倾斜保护。《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即规定,机动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致行人受伤,双方同等责任的话,机动车的赔偿责任比例为60%-70%,而非50%。[7]如果三者险条款约定以被保险人实际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进行赔偿的话,条款的效力是应当被肯定的。
二、高院案例中的争议
1 . 车损险中的按责赔付。部分高级人民法院的案例显示,对该问题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可保险合同条款的效力,另外一种观点否定条款的效力。
| 观点 | 案号 |
| 无效 | (2014)鄂民监三再终字第12号 |
| (2014)新审二民提字第00045号 | |
| (2016)宁民申57号 | |
| (2016)黔民申871号 | |
| (2018)内民申1860号 | |
| 有效 | (2013)闽民申字第1194号 |
| (2014)吉民申字第240号 | |
| (2014)闽民申字第645号 | |
| (2016)甘民申70号 | |
| (2016)内民申328号 | |
| (2016)新民申687号 | |
| (2017)川民申4195号 |
需要指出的是,(2014)鄂民监三再终字第12号和(2014)新审二民提字第00045号均是再审改判案例,这显示了湖北高院和新疆高院观点的坚定。
在(2014)鄂民监三再终字第12号案件中,湖北高院认为:
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机动车损失保险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当保险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负全部、主要、同等、次要责任的情形下,保险人分别按100%、70%、50%、30%的事故责任比例分别计算赔偿;第十七条约定:在应由第三方负责赔偿却无法找到第三方的情况下,保险人予以赔偿。但在符合赔偿规定的金额内实行30%的绝对免赔率。除此之外,双方对于如果发生本案情形,即投保人对事故无责任,而全责第三方也可以找到的情况,胡某某能否直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并无直接、明确的约定,双方对此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并产生争议。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于格式条款内容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对于双方争议问题,应解释为胡某某可以依据保险合同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退一步而言,即便如保险公司主张及二审判决认定的,可以从涉案保险合同第十五条和第十七条约定的内容间接推导出“无责不赔”的解释结论,也由于太平洋保险公司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与胡某某签订保险合同时,已经就该合同中的免除责任条款内容,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因此,本案保险合同中所谓的“无责不赔”的条款,依法对胡某某亦不产生效力。胡某某作为投保人,其在投保财产受到侵害受损时,选择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保险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该案中的条款应该是《机动车商业保险行业基本条款(2007版)》的C款。事实上合同第15条和第17条之间并不存在理解上的歧义,因为第17条明确了30%的绝对免赔率是针对“符合赔偿规定的金额内”。故无论将该条中“应由第三方负责赔偿”解释为“应由第三方全部负责赔偿”,还是解释为“应由第三方部分负责赔偿”,均不应当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结果。
此外,C款中明确“保险机动车一方无事故责任或无过错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湖北高院认为“除此之外,双方对于如果发生本案情形,即投保人对事故无责任,而全责第三方也可以找到的情况,胡某某能否直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并无直接、明确的约定”并不正确。因为根据该条款,保险机动车一方全责时,无论第三方是否可以找到,保险人均不承担赔偿责任。
该案再审文书并未对保险公司为何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作过多论述,此项的分析也就无从继续。总体而言,本案的裁判说理仍然是混乱的。当然,湖北高院观点是坚定的。
在(2014)新审二民提字第00045号案件中,新疆高院认为:
关于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按责任比例赔付”的条款是否属于无效条款的问题。申请再审人杨某某与被申请人保险公司所签订的机动车保险合同中约定按照投保车辆驾驶人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比例对车损进行理赔。该条款虽规定在保险合同“赔偿责任”条款中,但从该条款内容的实质进行判断,该条款的约定会产生限制或者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情况。因此,该条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被申请人保险公司答辩称该条款不属于“免责条款”的理由与该条款的实质内容不符,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关于“对免责条款应尽的说明义务”的规定,对于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应就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否则,该条款对投保人不发生法律效力。被申请人保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对申请再审人杨某某就上述按责任比例赔偿的条款履行了告知义务,故该条款对申请再审人杨某某不发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应按实际车损进行理赔。
本案中新疆高院的论述简单了许多。首先,该条款属于免责条款;其次,对免责条款保险人应当尽到说明义务;第三,保险人未尽到说明义务;结论,该条款对被保险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当然,该案中由于保险公司未提供证据,结果也就顺理成章。但如果保险人尽到说明义务,该条款的效力如何,该案并未阐明。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如何评判,本案也未阐明。
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高院在(2016)内民申328号案件中肯定了比例赔付条款的效力。而在(2018)内民申1860号案件中又否认了该条款的效力,是因为保险公司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这表明内蒙古高院不认可该条款属于《保险法》第19条规定的无效条款。
2 . 责任险中的按责赔付。案例及观点的情况如下:
| 观点 | 案号 |
| 无效 | (2013)甘民三终字第57号 |
| (2013)浙民申字第246号 | |
| (2014)新审二民提字第00045号 | |
| (2015)鄂民申字第02826号 | |
| (2016)晋民申279号 | |
| (2016)鲁民再130号 | |
| (2016)渝民申538号 | |
| (2017)辽民申4639号 | |
| 有效 | (2014)津高民申字第0363号 |
| (2015)津高民申字第0563号 | |
| (2015)新民申字第507号 | |
| (2016)皖民申1142号 |
在(2016)鲁民再130号案例中,山东高院认为:
本案中保险公司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十二条第一款关于“保险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保险人根据驾驶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负事故责任比例相应承担赔偿责任”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故保险公司关于上述合同条款不属于责任免除条款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山东高院的观点鲜明,论述简洁明了。相比(2014)新审二民提字第00045号案件的从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出发,这是另一种裁判的路径。
在(2015)新民申字第507号案件中,新疆高院认为:
因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赔偿义务系基于其与投保人之间的商业保险合同,故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投保车辆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时,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承担50%的赔偿责任;再扣减受害人自身承担10%的责任后,侵权人刘某某应当承担剩余40%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侵权人刘某某负事故同等责任,保险条款载明此时保险人按50%比例赔偿。法院最终认定侵权方承担90%的赔偿责任,受害人自负10%的责任,同时法院也认定保险人仍承担50%的赔偿责任,故另外40%的赔偿,侵权方无法从保险公司获得弥补,只能自己承担。
相比(2014)新审二民提字第00045号案件中对车损险按责赔付条款效力的认定,本案中的新疆高院保守了许多。新疆高院的思维无疑是车险行业条款变迁的真实写照——保险条款变我就变,保险条款不变我也不变。该案中,保险条款约定的“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是什么,新疆高院也未对此细致分析。如果认为本案中法院变更了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那么这里的“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是不是应当指法院最终认定的责任比例?如果将公安机关的事故责任认定和法院认定的赔偿责任相区分,这里的“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还是不是指公安机关的事故责任认定?
三、保险司法实践中的困惑
时至今日,最高院并未就本文的话题作出明确规定。裁判的分歧固然有着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之中更蕴含着方法论和法律规范适用上的难题。这些困惑,无疑是保险法免责条款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呈现的种种难题的一个缩影。具体而言,问题的成因如下:
成因一,《保险法》第17条和第19条的关系纠缠不清。
第十七条 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十九条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
(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
(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格式条款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私法世界的原有面貌。[8]实践中的保险条款基本上都是格式的保险条款。以保险整体运营宏观角度观之,保险人掌控保险产品信息、技术信息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信息,而投保人对上述信息很难获知。为解决信息偏在问题,赋予保险人相关信息的解释说明义务,从而平衡投保人与保险人在信息掌控中的失衡关系。[9]为此,《保险法》第17条规定了保险人的提示、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0、11、12、13条就如何认定保险人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至于第19条的规定,无非可从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两方面予以理解,即“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的格式保险条款无效,“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或者“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的格式保险条款也无效。对该条的所指的条款,不妨简称为“权利义务失衡的格式保险条款”。
从《保险法》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来看,保险人如果没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是明确的,即“条款不产生效力”,或者说是条款不生效。从逻辑上来说,如果保险人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则条款应当产生效力。
问题随之而来,对“权利义务失衡的格式保险条款”,如果保险人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是否产生效力?
在(2016)新民申687号案件中,新疆高院认为:
经查,保险公司向申某某提供的《家庭自用汽车保险条款》为格式合同。该条款赔偿处理部分第二十六条“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约定系免除了保险人的部分保险责任的免责条款。但保险公司在向申某某提供的保险条款关于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部分已用黑色加粗字体进行了突出标注。申某某在投保单中的投保人声明处签名,说明保险公司已向申某某送达了保险条款,并已就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约定的内容向申某某做了明确说明,申某某对保险条款已充分理解,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同时《责任免除条款特别告知》的投保人签章处也有申某某的签名和确认。上述事实说明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关于保险人按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保险公司已就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申某某履行了提示注意义务。虽然该条款约定驾驶人责任越小,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比例越低,但该约定并未限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向侵权人请求赔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请求侵权人赔偿。原审法院认定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的约定并未违反公平原则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该免责条款有效并无不妥。
本案中,新疆高院也认为“该条款约定驾驶人责任越小,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比例越低”,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向侵权人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所以权利不受影响。欲言又止的话语间,表明新疆高院还是立足于《保险法》第17条的适用。虽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向侵权人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就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而言,该条是否属于“权利义务失衡的格式保险条款”?恐怕,新疆高院也是持肯定意见的。因为保险公司的赔付能力优越,而侵权损害赔偿存在执行不能的风险,通过保险合同让保险公司赔偿,结果总比通过侵权法律关系赔偿更为可预见。
以本案与(2014)新审二民提字第00045号案件相对照,只能说新疆高院对《保险法》第19条的适用是排斥的。在新疆高院看来,私法贯彻意识自治的原则,约定即优先,约定了也就不存在“权利义务失衡”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面对格式的保险条款,完全可以“要么接受,要么走开”。对此,马宁老师揶揄到,“或许是基于对私法优越性的信奉而尽力维护其纯洁性的需要,我国私法学者多对内容规制持怀疑之态,而更青睐于信息规制。”[10]
从思维的逻辑层次上,这一问题可以分解为以下数个问题:
问题一,第17条所言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和“权利义务失衡的格式保险条款”在内涵和外延上是否一致,尤其是在“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同样为格式条款的情形;
问题二,如果“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外延大于“权利义务失衡的格式保险条款”,那么在适用第17条的规定后还有无第19条适用的空间。此时,如果保险人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第17条规定的“不产生效力”是否可以当然从逻辑的角度解释为“产生效力”。进而,“产生效力”后能否继续适用第19条的规定予以审查;
问题三,如果“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外延小于“权利义务失衡的格式保险条款”,是否意味着第19条的规定可以独立适用于第17条的司法实践;
问题四,在独立适用第17条的情形下,如果保险人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其责任边界何在?合同的解释规则在此时扮演何种角色?保险责任的范围此时如何界定?
成因二,《保险法》第17条和第30条的关系纠缠不清。
第三十条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保险法》第30条体现的是保险合同解释中的不利解释规则。不利解释的规则来源于合同法,又称“不利条款起草人的解释”。它在格式合同的解释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不利解释原则并非保险合同解释的惟一原则。
在格式条款面前,自由选择和双方合意的契约自由之应有内涵时常面临缺失的尴尬,以程序正义实现实质公平的契约自由之目标凸显实现不能之虞。[11]保险条款冗长复杂,专业术语较多,极富逻辑性。即便保险人愿意善尽说明义务,欲使投保人完全理解条款也是不现实的。针对这些问题,传统契约法的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救济措施力有未逮,各国遂开始以信息规制或内容控制的方法应对。[12]这在我国《保险法》上体现为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
《保险法》第17条和第30条在实践中呈现的冲突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对保险人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如果存在通常理解,第17条的法律后果能否适用?相关的困惑体现在车险的诸多领域。比如针对无证驾驶商业险是否赔偿即存在着几种观点。有观点即认为,无证驾驶虽为约定免责情形,但如果保险人未尽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仍应赔偿。[13]
第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12、13条规定,保险人的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均可采取书面的方式进行,即对认定保险人的提示、说明义务的认定采取了宽松的立场。在认定保险人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尤其保险人的意图足以在合同中明确时,有无不利解释规则的适用空间。比如(2016)粤民申1715号案件中,案涉的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7条内容为:“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伤害导致身故、残疾的,保险人也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四)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法院认为对该条款进行文意解释,其含义可以理解为:只要存在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驾驶证的情形,保险公司即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但同时,该条款并未明确指出无论导致身故、残疾的事故是何原因,只要存在该第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均不予理赔。最终仍认定条款存在歧义,适用不利解释规则。
当然这可以理解为不利解释规则本身适用的争议。不过,保险条款终究逻辑复杂,对保险条款呈现的复杂的逻辑结构,保险人有无需要明确说明,还是径直适用不利解释规则呢?典型的如车损险中的发动机进水不赔条款。投保人以整车价格作为保险金额购买了车损险,作为通常的大众,合理的期待应当是属于车损险的赔偿范围。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对条款的理解显然存在分歧。此时,是继续从保险合同的用词、相关条款的文义、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综合认定条款的真实意思,还是适用第17条的规定认定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14]
上述的问题在司法案例得到了充分展示,但却鲜有裁判文书予以澄清。马宁老师的研究向我们呈现了司法中的这种困惑——有法院先认定条款无效,随后又论证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因而条款不生效。也有同时认定一个条款未生效和无效;亦有先对条款做不利解释,后又提及该条款免除了保险人的法定义务;更有法院论证免赔条款既属于未说明而未生效,又属于排除被保险人权益的无效条款,同时还存在歧义,应作不利解释。[15]典型的案例如上述(2014)鄂民监三再终字第12号,案例中湖北高院同时使用了不利解释规则和提示说明生效规则。
成因三,《保险法》第19条的适用步履维艰。
对《保险法》第19条,最高院的法官认为:
《保险法》第19条难以取代第17条……由于第19条在主体部分未确立判断无效格式合同的依据,对以何种标准判断格式条款效力存在不同认识。实务中,不同法院对一些格式条款是否可以依据第19条认定无效容易产生争议。因此虽然对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理解与适用存在争议,但以一个尚不成熟且可能制造新问题的制度来取代它似乎也并不妥当。[16]在最高院的法官看来,第19条的规定是“不成熟”的,也“可能制造新问题”。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保险司法实践中的诸多争议足以证实这种担忧的正当性。但这种担忧也造成了《保险法》第19条的适用的步履维艰。司法中不敢用、不会用的现象较为突出。